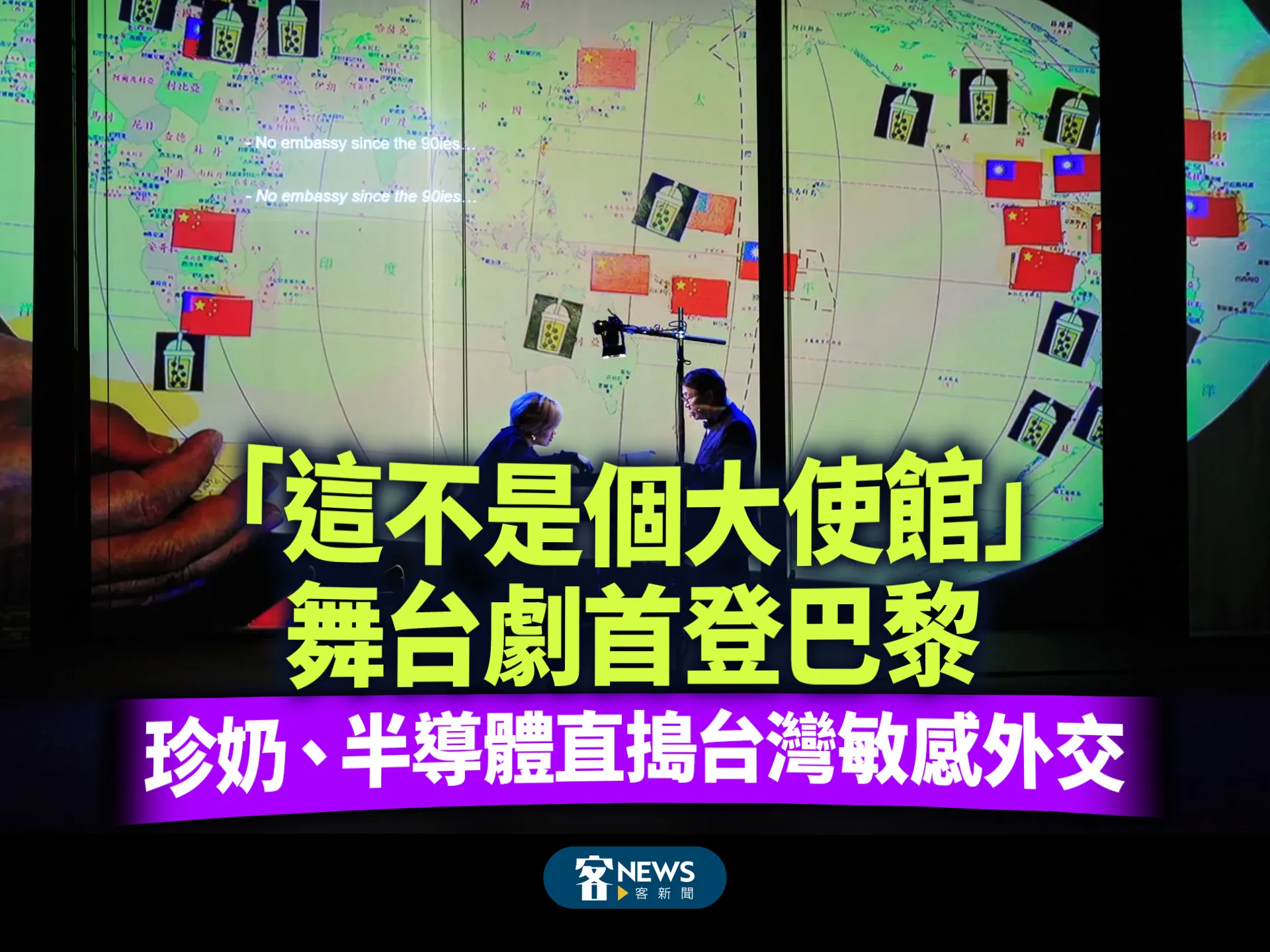【李台源、范修語/台北報導】音樂、影像、詩歌與劇場,可以融合成什麼樣的演出?長期投入族群音樂、影像工作的鍾適芳,從客家出發,用多媒體音樂劇場的方式,探討橫跨時代、地域文化的遷徙故事,創作成《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音樂影像現場,即將在兩廳院2024秋天藝術節演出。對於創作發想,鍾適芳直言,「過往的客家主題計畫,總是會被要求『向內看』,但客家經過長期歷史回溯,應該要對當今世界的『遷徙』、『移動』更加敏感」,客家有能力站在前鋒位置,看當今國際上的遷徙,這個劇場就是從客家看世界的嘗試。
走進鍾適芳的「大大樹音樂圖像」工作室,一面擺滿各式書籍的書牆映入眼前,門旁矮櫃放滿金鐘、金曲獎盃。鍾適芳的「大大樹」從1990年代起,開始將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引進台灣。同時,投入客家、原住民音樂製作,並跨足影像、辦影展,近年則開始拍紀錄片。在看似商業與市場當道的今天,仍秉持著對「議題」的重視。
用劇場說客家、海洋與世界的故事
櫃子裡的獎盃實在太耀眼,我們問起鍾適芳,哪一座印象最深刻?不過,鍾適芳卻給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答案:他沒有特別感覺。「我不喜歡參加頒獎,都交給同事,因為典禮很冗長。沒有這些獎,我還是會繼續做。」

「我們一直關注與『遷徙』相關的議題,以及遷徙在當今世界局勢下,呈現出什麼問題。」鍾適芳切入正題,談起創作《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音樂影像現場的故事背景。他回憶,發想初期,國際上有敘利亞內戰難民問題,大批難民湧向歐洲,「不管是水路或是陸路,就在歐亞非接壤處的地中海不斷上演」。「若沒有迫切的生存需要,沒有人會冒生命危險渡過海洋」。
這種生存的移動在歷史上未曾停歇。鍾適芳思考,如何透過音樂說這些故事,從客家移民的歷史連結當今的國際移動。不過,分享創作內容前,他先說起長期在客家工作上的觀察:「強調客家主題性的計畫中,例如在策展過程,我們總是會被要求向內看」。
「我知道這是長期失去話語權的一個結果,但我覺得當今客家除了向內看,或向根本溯源,客家經過長期的歷史回溯,我們長期在移動,然後被作為當成『客』,我們應該更能夠站在前鋒,去看當今的國際上的遷徙問題,我們應該對這件事更敏感。」鍾適芳在創作發想時,剛好遇到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的全球客家串流計畫。他思考,「我們可不可以談客家的過去、當今與未來?談我們到底自己在哪裡,我們會不會也在海上?」
鍾適芳特別說到「海」,因為客家人在18、19世紀開始,透過水路,從原鄉大量遷徙到世界各地,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南亞的印度、斯里蘭卡,非洲的模里西斯,甚至中美洲牙買加,都有客家人落腳的痕跡。
海洋,是串聯起世界客家的關鍵。

在印尼邦加島 看見客家移民先鋒
說明複雜的創作背景時,鍾適芳還提到全球串流計畫的另一位串流者吳庭寬,將印尼客家裔作家湯順利(Sunlie Thomas Alexander)的小說翻譯成華語《幽靈船》。湯順利出生在印尼邦加島,作品有著強烈的移民歷史影像感,內容也包括印尼當代的政治、族群問題。湯順利的小說帶給了鍾適芳很多靈感;此外,鍾適芳還提到另一位邦加島上的詩人西思旺托(Willie Siswanto),他是湯順利寫作上啟蒙者,雖然不是客家裔,但邦加島上有百分之六十的客家移民,西思旺托關注邦加島上的移工、錫礦工人,以及他們早年遷徙到邦加島的生活情境。
早年在邦加錫礦工人雖是契約工,但受到的待遇是苛刻的,在西思旺托的書寫中,他們的處境有如奴工。「在做創作時,除了文學作品提供的參照,邦加的歷史學者艾爾維安(Dr. Ahmad Elvian)、『僑批』收藏家魏金華所提供的歷史紀錄影像、書信,對我們『重回歷史的現場』非常有幫助。」
這次在劇場中擔任說書人的金曲獎歌手羅思容,在看過這些詩作、影像後分享,「湯順利的小說、西思旺托的作品,讓我們又拉近了與這些18世紀、19世纪的這些客家移民者的距離。他們移民到落腳在他鄉,可能是一個勞動生產者,經濟的一個支撐者,但他們的這些經歷的生存的過程,卻很少被書寫出來。」
羅思容解釋,台灣有大河小說,包括李喬、鍾肇政與鍾理和等作家都有許多著作。但實際上,落腳在世界各地客家,文本卻非常欠缺,「這一次透過文本,讓我們真的再次相遇」,羅思容有感而發地說,也許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經歷同樣的時空,鍾適芳把議題、文本結合在舞台上,讓大家可以感受到客家作為一個先鋒者的角色。

對於找來羅思容一起合作,鍾適芳說,他與羅思容認識相當長的時間,甚至羅思容的第一張專輯《每日》,就是由大大樹發行。「思容不僅能夠掌握音樂現場,思容本身是詩人,而詩是這個作品中重要的敘事元素,因此是扮演說書人的不二人選」。
故事從海上開始 很多人卻沒上岸
《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三幕,分別是港(Ports)、 批(Surat,書信)與鬼(Ghost)。鍾適芳團隊透過田野調查與故事採集,交錯展現在劇場舞台上。表演者自身的族群身份與觀點,重組聽說故事角色,最終產出串連幾個時代、跨洲界與地域文化的遷徙故事。
鍾適芳在受訪時,特別強調「港」、「邊界」與「海」。「港是離開、航向希望的可能。你可能擠上了一艘船,從一個港漂泊到另外一個港」。鍾適芳蹦出了一句「但,到底能不能上岸?」在這個作品中,除了從港到港的漂浪,也記寫那些無法上岸,「還在水裡」的渡海者。
到底什麼是上岸?鍾適芳說,「很多人從港離開,但終究沒能上岸」,這是我們在創作、思考的過程中,不斷與主創藝術家碰撞出如何呈現沒有上岸者的身影與聲音。對於上岸與否的定義,羅思容則分享了另一種視角,如同許多從南洋寄回家鄉的照片檔案,「他們會到照相館,穿正式的衣服拍照片寄回家,讓大家看到它,可是在這些照片的背後,他們的生活卻是有百般的生存困境」。
讀了這些家書、羅思容想到了自己的祖先渡過黑水溝落腳台灣,「薄紙值千金,對於現代人手一機,隨時可以跟世界往來,以前一封家書就是一個極為珍貴的生命訊息」。
至於劇場的呈現方式,鍾適芳解釋,他的詮釋手法用的不是傳統台詞形式的腳本,而是以音樂現場、文學、歷史檔案、影像串起一段一段故事。鍾適芳與各個音樂家、藝術家討論光影、音樂與影像如何呈現。「當然,我必須先寫出腳本大綱,參與的藝術家才知道如何共同推展敘事」。
「它有一個故事,但不是以台詞敘說的故事」。音樂、影像、詩文,透過羅思容擔任的說書人,串聯「此時彼地,彼時此地」的時間與空間。面對抽象的呈現方式,鍾適芳說,他與主創藝術家有長期合作的默契,「我清楚每一位參與藝術家的特質,且他們也都關注離散、身分與當今難民的議題」。

音樂統籌的角色,由德國作曲家、鋼琴家Matthias Frey擔綱,客籍音樂家鍾玉鳳也參與部分音樂創作及演出。此次呈現更邀請到敘利亞打擊樂手Shadi Al Housh。Shadi曾冒著生命危險渡海,逃離敘利亞戰火,經歷無國無定所的難民身份,「除了精湛的打擊樂技藝外,Shadi也以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參與這個作品。」
藝術是面鏡子 照見真實世界面向
對於是否希望作品能給觀眾什麼樣的啟發?鍾適芳分享,《我們在此相遇》的前期展演時,多半觀眾不懂客語,也不懂印尼語,卻都能感受到作品所要傳遞的內涵與精神。「每個觀眾都可以選擇,如何回應則與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
羅思容則語帶嚴肅地回應,當今世界的許多議題,我們以為會走向好的方向。實際上,包括戰爭、性別、勞資、乃至於氣候變遷等等,許多卻是往負面方向發展。作為藝術創作者,如何把作品當成鏡子,照見人類真實的生存處境,如實照見世界更多的面向、照見沒那麼甜美的內容,「至於照鏡子的人感受到什麼,或有什麼回饋,當然是開放、尊重,就讓大家自行發酵吧!」
鍾適芳則補充,我們現在擁有的平和與安逸是很脆弱的。長久以來,台灣在國際上沒有明確的身份,總讓我們期待別人能看見我們,然而我們卻不太在意別人的歷史,或者當今世界正發生的事,總覺得一切都離我們很遠。
為什麼我們從邦加島的書寫來回看我們自己?鍾適芳說,這是對我們有幫助的事情,不然我們真的就在這個小小的島上面,這齣戲是一個多元的視角,「它可以從島望向海洋,也可以從海洋望向島嶼。我們渴望的是提出更多生命的可能性,生命不是一個為二、為幾的形式,它可以很多元」。
為何我們從邦加島的書寫來回看我們自己?鍾適芳說,他幫助我們開展更為多元多向的史觀及敘事的可能;羅思容則補充說,「它可以從島望向海洋,也可以從海洋望向島嶼。我們渴望的是提出更多生命的可能性,生命從來不是一個唯二或為唯幾的形式,它可以很多元。」
「我很感謝台灣這片土地,它可以讓我很自由的創作,這是台灣可貴的地方。只是,我們希望它能有更多的可能性,不會被政治的緊箍咒去框限它更多可能。」羅思容說,「藝術的可貴、藝術的力量,就是它可以自由的,去把我們的想像跟渴望放在創作裡,這個作品無論是放在台灣,或者其他國家,同樣都可以觸動人心。」

2024秋天藝術節《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音樂影像現場
日期:2024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
地點: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購票連結:https://lihi1.me/ZmZ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