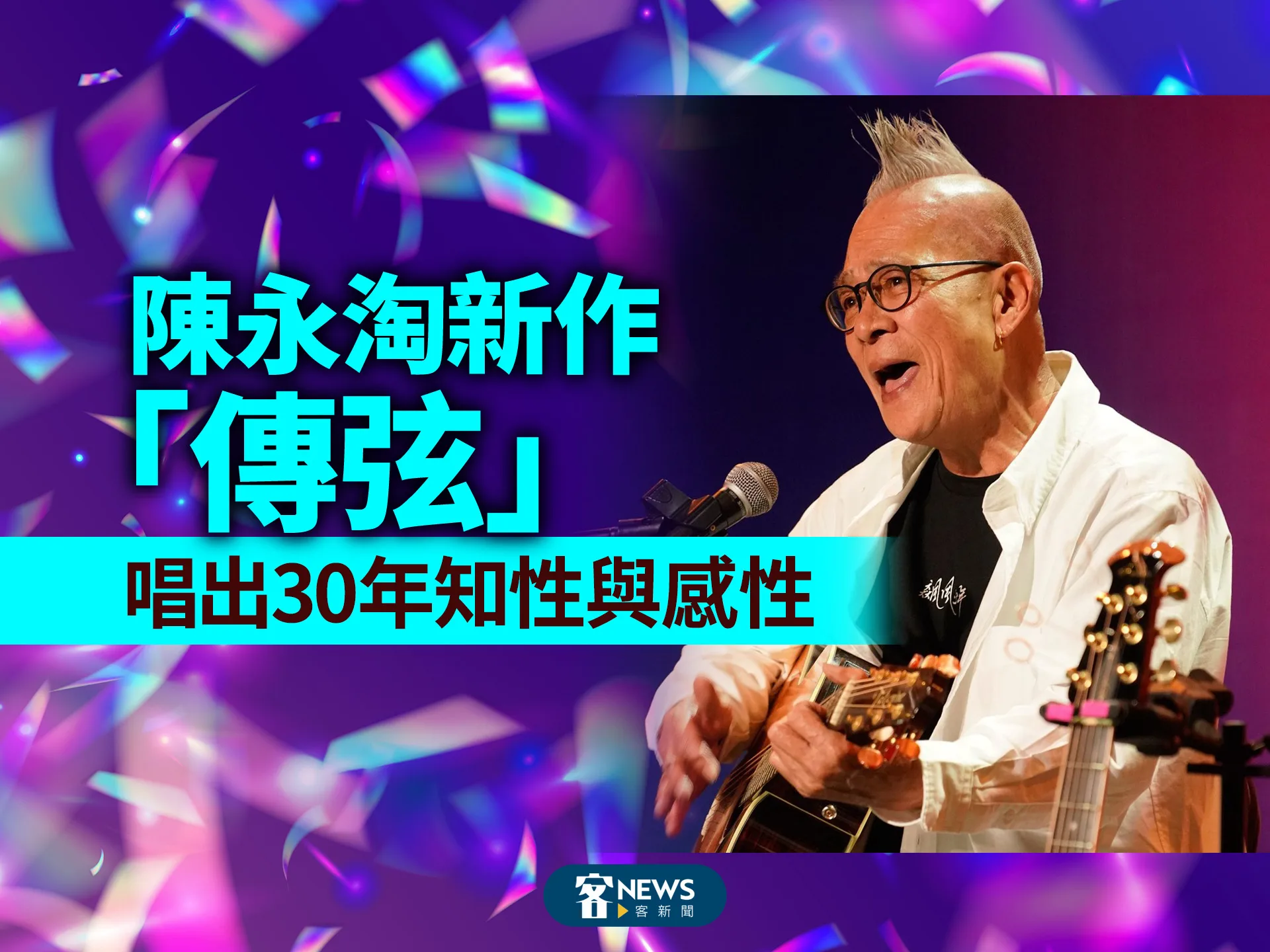文/楊長鎮(客家委員會前主委)
《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是一奇特的寫作,她在文體上令人疑惑,在內容上引人迷失。
疑惑是因為不知道該以閱讀歷史或以閱讀文學的態度來面對,致於進退失據、 無以自拔。
迷失是因為故事在時間中的前後跳躍、在空間中的左右穿梭,引領讀者進入一段陰鬱奇幻的旅程,讀畢而不自知所終。
先談文體。作者很明確地自述其藝術企圖與一種身在其中的敘事立足點,一定程度上與歷史研究「劃清界線」。但與歷史工作者相較而毫不遜色的紮實田野調查作業 ,確實啓動了讀者的歷史想像能力,而歷史想像也確實是史家技藝中很重要的素養。以一個藝術領域訓練背景的作者而言,這是值得肯定的一大成就。
文體對文學創作者而言經常是需要被踰越的框架,或者說,踰越框架乃一切創作的本質。文體經常提供讀者想像力的依靠與限制,其實,對創作者亦然。勇敢的創作者遂必須敏感到能充分實踐其創作意念的適當形式。
最近,作品被拍成電影、獲得文學獎肯定,且由美國知名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小說英譯本的陳耀昌醫師,他的「小說化的歷史」寫作卻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文、史學界一些嚴苛的批判。在一個開放社會中出現不同意見毋寧是正常的事。我關注的是,以文學形式進行歷史企圖的書寫可以走多遠?以陳耀昌的作品而言,他同樣也經由大量的文獻與田野調查建構他的歷史想像,再以小說的形式表現歷史書寫無法達到的情感形式。他的踰越實驗誠然是危險的,但對創作者而言,誠意的創作即使面臨負面批判都是值得的。
另外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案例是李喬。他的鎮山之作《寒夜三部曲》 展現他下足苦工的歷史調查能力,《結義西來庵:噍吧哖事件》等歷史小說書寫延續了這種考證的基礎工夫。到了《埋冤. 一九四七.埋冤》,他的文體之歷史書寫化已讓人困惑:這是在寫歷史還是在寫小說? 有位資深創作者即曾對我表示質疑與否定之見,認為無甚藝術價值。但在我來看,這種大膽的「歷史化的小說」文體以冷靜、中立、理性到甚至接近乾枯的書寫策略,製造了巨大異常的張力,把二二八歷史的大痛無悲、大悲無言發揮到淋漓盡致。重大歷史事件的文學處理是挑戰性的任務,一不小心就會傷害了歷史的嚴肅與重量,李喬以文字操弄的最大程度收斂向歷史致以最高的虔敬。這與他在諸多短篇小說中展現幾不重複的靈活多樣「技法」呈現強烈反差。
如果說李喬的「歷史化小說」刻意製造一「我的不在場」情境突顯歷史的巨大宏偉與深沉,則本書作者的策略可說是以「我的在場」突顯人作為歷史性存有的深刻自省與自我追索。他在田野訪查筆調中不以客觀中立的歷史研究者身分出現, 他以訪問、詢問乃至質問讓自我逼臨歷史現場,更精確地說,是逼臨歷史性的衡突與悲劇的現場,以致於叩問陰魂、行走於死亡的蔭谷。這種「有我之境」的書寫讓土地的歷史與主體的建構串接,也因此宣告了與歷史研究的分道揚鑣,創作了自成一格的創作形式,遂能自由地穿梭時空證成「我之為我」的立足點。
從這裡開始,我們隨著作者的自我追索而自我追索。尤其對作為北台三線成長的讀者如我而言,從閱讀中剖露意識與困惑,展開夢遊般的飄蕩,這像是一種儀式過程,如在上下,如在左右,在作者不同章節中不斷主題重現的文字中若即若離。
作者以自己成長地區與左近範圍調查並發現「我」作為歷史事件的發生現場。他首先反思了北台三線這個場所作為原漢交錯邊界帶來的存有的疑惑(puzzle)與困惑。適巧因為政府推動「浪漫台三線」的時空巧遇,他以此作為一個可以立足的對立面,或者說是對話對象,展開了追索的旅途。質疑漢人社會「開山打林」的拓墾定居者歷史敍事,是本書的書寫基調,但作者亦雅不欲此作淪為廉價的懺悔, 因此而尋求從不同的族群/空間方向推近「海峽中線」,作為自我的歷史協商。
這樣的協商很適切地從「他者」的歷史(或沒有歷史)場域展開,以一個台三線客家人出發,前往鄰居泰雅族的領域拜訪。這個拜訪嘗試理解原住民生存空間發展、變遷脈絡,及在此生存空間之生態與歷史動態中形成的生存方式與社會文化。這部分大抵不出一般的研究成果,但為讀者提供了人類學式多元價值思考方式,對習於自我族群中心敘事的讀者而言,舖陳了兩大族群在台三線時空中相遇與碰撞的原初情境。
接著,作者遍訪今日桃園的大溪、龍潭,新竹的關西牛欄河、馬武督,霄裡溪、鳳山溪流域等地,這些「能近取譬」的廣義家鄉,沒有一尺不是原住民族曾經生活的空間,也沒有一吋不曾是族群相遇的殺戮戰場、流血之域。
如果一定要尋個根柢究竟,人世竟無一處可云浪漫,尤其現代世界的形成基本上就建立在對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侵犯與屠戮之上。作者想強調的是,台灣漢人定居殖民體制對生存空間擴張的需求勢必以侵犯原住民族領域為基礎,而燒耕、遊獵的生計經濟生產使原住民族發展出與特殊生態條件共存的生活方式,而在定耕文明侵入過程發生了歷史的不幸。土地觀、生態觀與產權觀的不協或矛盾,使這片土地成為異族遭逢的流血之地。
在承認與發掘作為定居殖民侵略者後裔的同時,作者也從自已祖先或先民在蓽路藍褸中不祥的斷頭記憶看到歷史的創痛與遺憾。對漢人常民階層的遭受「番害」歷史記憶,作者若得其情,對父老們的傷慟拳拳致意。這同時也是作者對自己先人歷史處境下的人性表現尋求理解的可能,藉此理解或可作為某種救贖。
以頭顱為中心,作者理解馘首作為泰雅族gaga文化中的宗教性與嚴肅性,相對而言,漢人對於無頭祖先的不祥象徵與傷慟,成為歷史作為一體兩面或遺憾的循環。人群邊界映照人性邊界,這不正是人類共同歷史的寫照嗎?
在「兩案並陳」之外,作者猶有進者。我相信在本書的一切寫作題材中,作者最用力企圖引發讀者不安情緒以作為歷史反思策略的,應該是漢人吃番肉的歷史事實。雖然未有明言,但我相信一定程度上,作者企圖以立基於生態與宗教的嚴肅性,對照原住民馘首與漢人吃番肉、熬番膏的粗殘野蠻。
在這裡,我想重引述本書作者與其他論者都重視的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中觸目驚心的一段:「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在其他的傳說或記述中,漢人吃番肉似乎一開始是隘勇的秘密,帶有取其精力的迷信與恐懼色彩,但胡傳揭露了,食番肉、番膏是常民公開參與且至於市場化、有行情的。在其他記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台灣番肉以塩醃製、水缸運送、出口至廈門。因此,所謂的官示禁徒為虛文,非制度性的行為成為一種普遍實踐的社會文化。這種超出個人私密或血讎的行為完全不具犯罪意識,而成為一種合理化殺番行為的集體自我正當化,其內核則是將 「生番」的非人化。當「番不是人」的意識被建立起來,所有的侵略、佔有與殺戮都成為文明向前推進的腳步。這一層認識只在作者文字的無意暗示之中,有賴讀者舉一反三自省之。
作者以河川襲奪、斷頭的地理意象作為不堪歷史的出土現場,以這種赤裸裸的自省回顧歷史為祭儀,同時向不同族群先人致以敬意與遺憾。也因此,書寫與創作的祭壇上,承認並發現自我之所來成為最赤嚴的祭品與救贖。
附帶,我想討論作者歷史理解的兩個議題。
首先是關於「定居型殖民」作為本書重要的結構性詮釋基礎。定居型殖民主義或名為拓墾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通常我們將這概念與掠奪型殖民Exploitation/Extractive Colonialism及貿易型殖民主義(Trade Colonialism)相對照,在台灣歷史上,這三種我們都經歷過。荷蘭與西班牙在台灣建立對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飛地,此貿易殖民的基礎上,荷蘭人招徠漢人種植甘蔗以製糖出口,種稻供應內需食糧,並控制原住民部落以壟斷鹿皮貿易,三種殖民一開始就互為支撐。清代平原地區的「開發」顯然是拓墾者尋求定居的殖民,但對糧食不足的殖民母國出口稻米卻是對拓墾影響至為重大的因素。北台三線的武裝殖民拓墾,非常重要的動力是對山林資源掠奪,及進入國際貿市場,如清政府所需要的軍工料樟木,中國內地所需的藤與鹿肉脯,最重要的則是樟腦掠奪。後來國際茶貿易市場則支持了樟樹耗竭後的貿易需求。
也就是說,原漢二元的殖民結構揭露了一部分歷史圖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是北台灣內山「開發」的另一大動力,從「番社」到「民莊」的社會地理演變則是這個複層殖民的結果。人作為歷史行動的主體而存在,亦作為歷史結構的客體而存在。從能動與被動兩層意義上,理解人在歷史中的有限性與責任性,成為多重殖民史下的我們的重大功課。
人尋求在歷史中的存在意義,或殖民後裔尋求在殖民史遺緒中的存在意義,這是現代理性主義尋求客觀歷史重建所不及的空間,對這個空間的理會、追索,無疑是一種人性的、浪漫主義歷史的衝動。
編按:本文由游擊文化授權刊登